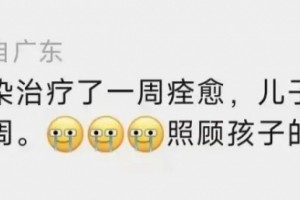雪衣豆沙,温暖甜美的故土滋味
作者:艾 英(江苏)
前些天刷朋友圈,看见侄女在微信中写:“想吃爸爸做的雪衣豆沙了……”我在她文图下面留言:“我喜爱吃你爸爸做的雪衣豆沙,也喜爱吃你爷爷做的雪衣豆沙。”侄女回复:“我历来没吃过爷爷做的。”“是哦,你是1984年春天出世的吧?你爷爷1980年秋天就生病了……”
我与侄女在微信中聊得挺亲热,也挺伤感,说到“雪衣豆沙”这几个字,激起我心里的一片涟漪:父亲熟练地滚动一锅油汪汪、金灿灿的雪衣豆沙的景象,停留在年月深处;哥哥端出一盘热腾腾、香馥馥的雪衣豆沙的画面,镌刻在生命旅程;全家人聚在一同,力争上游吃雪衣豆沙的场景,在回忆中鲜活、生动。
我出世于上世纪60时代中期。小的时分,家里与大多数家庭相同,日子不是很殷实,但在长春某饭馆当司理的父亲,有一手煮饭做菜的好手艺。父亲是个大忙人,成天不着家,长在饭馆里,平常家里的饭菜都是母亲做,只需新年、过节时父亲才会掌勺做年夜饭,也会先做出一道雪衣豆沙给全家人吃,由于这道点心涵义甜甜美蜜、团团圆圆。
比我大五岁的哥哥和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对这道点心是什么感觉、喜爱与否我不清楚,乃至也历来就没问过他们,但是我特别喜爱吃这道绵软甜美、耐人寻味的甜食——不要说吃,一想到它,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雪衣豆沙,也叫雪绵豆沙,是吉(林)菜和东北菜的经典甜食,起源于东北满族、清朝宫殿御宴,已有上百年前史。制造流程与工艺精密、考究,制造进程杂乱、繁琐,费时、吃力、费油,一定要现做、现炸、现吃。
每次做时,父亲总是独安闲厨房繁忙,只知道做雪衣豆沙用到的主要原料有红豆、鸡蛋、淀粉、面粉、猪油、白糖等,都是手艺制造,但详细怎样做的,我并不知道。只听到筷子敏捷在碗里搅动鸡蛋清的声响,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跑到厨房,往炉前凑。因火大油热,父亲怕溅到我脸上和身上,总是吩咐我:“离远点。”有时,乃至呵责——“别过来!”所以我总是小心谨慎地看着,至今也不会做,这是一个惋惜。
通过漫长的着急的热切的等候,等父亲把刚出锅冒着热气的雪衣豆沙装在盘中,撒上白糖,咱们刻不容缓地蘸着白糖,一口咬下去,半糊状的豆沙馅烫嘴——我差不多每次都被烫到,但下一次仍是这样急迫。雪衣豆沙有必要趁热吃,刚炸出来金黄、圆润、顺滑,假如放时间长就凉了、软了、瘪了。第一个总是饥不择食,感觉外酥内软,有点弹性,因不油不腻,有点骑虎难下。但吃最终一个就细嚼慢咽,让甜美、鲜香、油炸的滋味在口、舌、鼻之间,旋转、旋绕、充满……
哥哥是男孩子,身体好、能吃(后来做运动员、成为武士、当厨师);我最小也最馋,一到这时就胃口大增,吃到舔手指停止;姐姐性情温和,不争不抢。妈妈更是让着咱们,不怎样吃。我乃至觉得,人世间最美的滋味便是雪衣豆沙,每年能吃到一次,就称心如意。父亲做这道点心要花好长时间,而几个孩子总是风卷残云,一瞬间时间就消除净。每次吃完雪衣豆沙后,家里飘着的豆香、蛋香、油香,还有热气和甜美气味,久久不散。
1980年秋天,父亲患沉痾,手握不住筷子,再也不能为一家人做雪衣豆沙了。
父亲生病后不久,哥哥从部队转业回长春,也在饭馆作业,先做厨工,后做厨师——28岁成为三级厨师,后来还自己开过一段时间的饭馆。
在我脱离长春到北京读大学的几年间,哥哥也会做雪衣豆沙,有在饭馆的勤学苦练,应该也得到父亲的“真传”。每年寒假回家,正赶上过新年,哥哥顶替父亲掌勺全家的年夜饭,也会先做一盘雪衣豆沙给家人垫底。我看过哥哥做这道点心的进程:将鸡蛋清搅打至干性发泡,参加淀粉拌和均匀,做成蛋泡糊;勺内放入猪油,用筷子夹着现已揉好、沾满面粉、蘸满蛋泡糊的豆沙团子,挨个下入热油中;用热油轻浇,白色的雪球在起浮,直到炸成金黄色捞出,放在盘子里,撒上白糖,就可以吃了。这时,父亲也会尝上一个,渐渐地吃。有时点点头,说声“不错”;有时摇摇头,渐渐地说,“还差点火候……”
2001年5月末,母亲逝世了。2006年大年初二,父亲逝世了。
我仍隔几年回长春一趟,看望垂暮的姑姑,陪同年岁渐渐的变大的哥哥、姐姐,每次都住在哥哥家。知道我爱吃这道点心,只需我一回去,不管什么时节,哥哥都要特意做一次雪衣豆沙。
其实,这些年在江南日子,我知道常州有一道名点,叫“网油卷”。与“雪衣豆沙”称号不同,但用料、形状、口味大体类似。我在一些饭馆吃过屡次,细密绵软,甜美松鲜。但说来也是古怪,我不吃时历来也不想,心心念念的仍是雪衣豆沙。总觉得这儿的网油卷与家园的雪衣豆沙,尤其是与父亲和哥哥做的雪衣豆沙,如同差点什么。但是,差点什么呢?
2017年秋天,我休半个月公度假,再次回到长春。住在哥哥家,他家楼上住着侄女一家。哥哥年近花甲,眉毛、眼睛、神态与父亲几乎一模相同,尤其是满头白发、白色眉毛,看着心酸、疼爱,又想起父亲,不免伤感。哥哥要做雪衣豆沙,我不忍心让哥哥多劳累,劝他不要做了。哥哥说,不费事,豆沙馅有现成的卖,不必自己弄。再说,你侄女和侄孙女(侄女的女儿)都和你相同,就好这一口子,外面饭馆做的不吃,偏要吃我做的。
我一边与哥哥聊家常,一边细心地看他用筷子打蛋清:他分三次参加白糖,直到把蛋清彻底打发至发白成雪花状,筷子立在碗中不倒——哥哥说,这是你回来了我就手动打发蛋清,平常做用打蛋器。手动打发太累,也费时间。我方想起,小时分不知道吃过多少次、多少个雪衣豆沙,只知道好吃,从未想到父亲做这道点心的辛苦。
哥哥往锅里倒一些油,烧热之后,把裹上蛋清的豆沙团子放里边炸,一瞬间转小火。他告诉我,做这道点心的关键是火候要把握好,油温不能过低,也不能太高,下锅后等外表定型漂起来,再略微有些焦的时分就捞出来。
一盘雪衣豆沙上桌,我和侄女、侄女的女儿三代人一同吃。一口咬开粘着白糖的外皮,再细细咀嚼,豆沙馅和白糖像雪相同在嘴里渐渐消融。清甜、酥糯、鲜香,细密、绵软、柔软,与小时分的滋味一模相同——从父亲制造到哥哥制造,嘴里、胃里,心里、梦里都是原汁原味;鲜甜美美的滋味、浑厚漫长的口感,经年流通,不曾改动;从幼年到青年,从中年到晚年,我已是不能多吃甜食的年岁。这道东北名点高糖高热高油,但我的毅力在这道美食面前早已一触即溃。
与我同年的嫂子也会吃上一个,而哥哥却是一口不吃,他血糖高,不能吃甜食,任劳任怨做这道点心仅仅为一家人,与父亲当年为一家人相同——假如父亲知道在他和母亲脱离人世后,他的儿女们还“常(州)来长(春)往”,而且日子过得渐渐的变好,他也是欣喜的吧?
我总算理解,为什么感觉东北长春的雪衣豆沙与江南常州的网油卷不同:由于雪衣豆沙是我生射中的专属甜品,于我的人生有特别含义,承载我幼年高兴、温馨、美好的韶光。那些一般、朴素、本真的日子,即便艰苦,也是苦中有乐、苦中有情、苦中风趣;雪衣豆沙不是一种一般的点心,而是用心血凝聚而成的食物,蕴藏至亲至爱的真诚情感,浸透漫长悠远的温馨回忆。每一次吃绵软可口的雪衣豆沙,都回想小时分的滋味;每一个喷香扑鼻的雪衣豆沙,都凝聚亲人的劳动;每一次想起那些时代悠远的日子片断、其乐融融的家庭场景,怀念故土之情激烈动摇,怀念亲人之情难以言喻。
雪衣豆沙,溢于齿间,渗进味蕾,百吃不厌;雪衣豆沙,用亲情和爱做成,不止时间短地安慰肠胃,更持久地温暖心灵。
本文刊于2020年4月11日《吉林日报·东北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