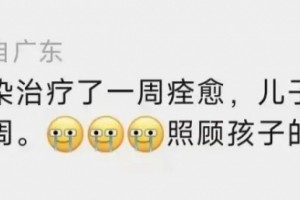基斯·范·希林根(Kees van Heeringen)见到瓦莱丽之前,这个16岁的女孩刚刚从桥上跳下。那还是1980年代,范·希林根在根特大学医院的物理康复科担任实习医生。瓦莱丽纵身跃下之后失去了双脚,已经在医院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整理了瓦莱丽跳桥自杀之前发生的一些触发事件,包括与周围人的紧张互动,抑郁症状的持续累积等等。
范·希林根后来在《自杀行为的神经科学》(The Neuroscience of Suicidal Behavior)一书中描述了这段经历,他说瓦莱丽的故事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96年,他成立了根特大学自杀研究中心,从此致力于推动诸多自杀问题的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同样困扰着他自己和其他人,而许多答案仍难以捉摸。
目前,很多国家的自杀率正在攀升。自杀已成为全球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估计,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
自杀本就复杂又悲惨。自杀相关的行为有很多种形式,从自杀意念或自杀想法,到自杀尝试和自杀行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与不同程度的暴力或暴力意图相关。这些行为在性别、种族和其他人口统计类别中的发生率是不同的,而且几乎都是在抑郁或者其他心境障碍的背景下发生的——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心境障碍患者会自杀。
任何科学研究领域,都无法单独解决像自杀这样复杂的现象。但是科学家们希望通过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深入研究自杀想法和自杀尝试,从而揭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研究基于这样的想法:自杀行为与特定的生物化学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可以独立于精神疾病(也可能与精神疾病同时存在)进行测量和靶向治疗。研究人员希望,这项工作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治疗方法,甚至可能有机会及时识别出处境最危险的人来进行干预。
麦吉尔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盖斯塔罗·图勒奇(Gustavo Turecki)说:“如今我们掌握的知识要比20年前丰富很多。我们已……在理解自杀问题的复杂性、神经生理学以及自杀原因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图片显示的是研究自杀采用的不同研究方法。有的研究控制了精神疾病变量,而一些没有;不同的研究侧重于不同的大脑区域;很多研究都只是初步发现。
—
LISA CLARK
大脑的压力通路在自杀中的作用
瓦莱丽描述的经历和许多试图自杀的人有相似之处。她表现出抑郁和社会应激的症状,而且正如范·希林根后来发现的那样,她还有自杀的家族史(自杀行为的一种已知的危险因素,与任何精神疾病无关)。
科学家们目前通过应激易感模型(stress-diathesis model)来思考自杀风险。该模型认为自杀有两种不同的诱因:一是促发因素(precipitating factor),如高压力或心境障碍;二是易感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如家族史、特定的基因变异或者童年不幸(例如受到虐待或忽视)。精神病学家和转化神经学家约翰·曼(John Mann)解释道:“自杀不仅仅是极端抑郁的状态。”他和神经生物学家维多利亚·阿兰(Victoria Arango)一起建立了这一概念框架。
该概念框架有助于研究大脑应激反应的生物化学通路,以及如何改变自杀人群的这些通路。大脑有多种应激反应,但在有关自杀的研究中,最为丰富的是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研究。HPA轴控制应激激素皮质醇的释放,而且会在临床抑郁症中被上调。
有关自杀和HPA之间联系的早期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死因的人,在自杀身亡者的大脑样本中,有着更高水平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CRH可以促进合成皮质醇,以及其他种类的糖皮质激素,这些激素均参与应激信号的传递。其他研究也表明,那些死于自杀的人有着更大的肾上腺,这正是产生皮质醇的部位。然而,由于自杀人群中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的发病率很高,此类研究并未试图确定所观察到的影响是自杀特有的,还是更普遍存在于心境障碍中。
最近,图勒奇等人的研究证实了HPA轴在自杀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即使在精神疾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童年不幸也是自杀的最大危险因素之一,它会对HPA轴的功能产生长期影响。在2000年代中期,图勒奇与麦吉尔大学的遗传学家摩西·西夫(Moshe Szyf)合作,后者发现被母亲忽视的大鼠的海马体(与压力、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大脑区域)的表观基因组发生了改变,而HPA对应激的反应也出现功能失调。图勒奇、西夫及其同事发现,相比于健康对照组以及死于自杀但未受虐待的对照组,在有童年虐待经历的自杀身亡者的海马体中,编码糖皮质激素受体(NR3C1,能帮助抑制皮质醇信号)的基因的表达降低,而且有被甲基化*修饰的痕迹。
*译者注
DNA甲基化是DNA化学修饰的一种形式,能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改变遗传表现。为表观遗传编码的一部分,是一种外遗传机制。
之后的研究将自杀行为与其他HPA相关基因的甲基化异常联系了起来。2018年,一项对近90名试图自杀的人进行的评估发现,在一些被试的血液样本中,CRH基因的甲基化程度降低;具体而言,这些被试的自杀手段更严重,也更致命。几项研究已经发现,与健康对照组和患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非自杀患者相比,自杀身亡者的SKA2(与NR3C1相互作用的蛋白质的基因编码)的甲基化水平较高,表达活性则较低。
HPA轴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例如,有的研究表明,自杀身亡者的HPA轴对压力过度反应;还有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图自杀的人皮质醇基线水平较低,且/或HPA对压力的反应迟钝。“这些文献令人困惑,”精神遗传流行病学家纳丁·梅尔亨姆(Nadine Melhem)说。几年前,梅尔亨姆发现,在父母患有心境障碍的约200个人当中,那些尝试自杀的人HPA活动总体较低。“几乎每个(可能的)发现都被发表了。”
梅尔亨姆指出,相关文献的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小样本和实验设计的差异。但是差异也可能来自于不同人群自杀行为的驱动因素不同。曼恩研究组在去年报告称,在35名试图自杀的人中,只有那些在性格测试中冲动性攻击得分较高的人,与没有自杀倾向的对照组相比,他们对压力的皮质醇反应明显升高。几年前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在对40岁以下人群的研究中,皮质醇水平与自杀行为风险呈正相关,但在对老年人的研究中,二者呈负相关。
5-羟色胺和其他神经递质的作用
在研究大脑化学的一个不同角度时,曼恩开始对自杀的神经生物学产生兴趣。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他和其他人发现,相比于死于其他因素的人,自杀身亡者(不论是否被确诊为精神疾病)的大脑中缺乏5-羟色胺信号,而且5-羟色胺的主要代谢物5-羟吲哚乙酸(5-HIAA)的含量也较低。曼恩说,这些发现是认识到自杀可能会有生物化学变化的关键。从那时起,5-羟色胺能系统就成为探索自杀倾向的神经递质系统之一。
和HPA轴类似,5-羟色胺信号似乎也受到童年不幸的调节。例如,在遭受童年不幸的儿童体内,编码5-HT2A受体的HTR2A基因出现甲基化改变——尽管尚不清楚这些变化如何影响HTR2A的表达。2016年的一项针对英国双胞胎的研究表明,遭到欺凌的孩子与未受欺凌的孩子相比,SERT(该基因编码将5-羟色胺从突触运输回突触前神经元的蛋白质)出现了高度甲基化。研究还发现,被欺凌的儿童对压力的皮质醇反应比较迟钝,这暗示了5-羟色胺能系统和HPA功能之间的联系。
这种生理变化如何影响自杀行为还有待观察,但是像曼恩这样的研究组正在努力解开一些细节。例如,在他和同事们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中,就阐述了5-羟色胺和HPA轴活动之间更具体的联系:即使在精神病诊断得到控制的情况下,5-羟色胺受体5-HT1A的水平也与皮质醇对压力的反应有关。研究组还对表现出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以及非抑郁症患者的5-羟色胺受体水平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无论精神病诊断结果如何,试图自杀或者死于自杀的人,其大脑皮层某些区域的5-HT1A水平高于对照组。
曼恩解释说,5-HT1A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5-羟色胺信号的缺失,这与我们的直觉有些不符,因为这种受体是神经反馈反应的一部分,它会抑制5-羟色胺进一步释放到突触中。因此,在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身上,“问题不在于制造5-羟色胺的能力,而在于利用5-羟色胺的能力”。5-HT1A这个角色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释,为什么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比其他抗抑郁药,能更有效地抑制自杀想法和行为。他补充说:在其他的一些影响中,SSRIs减少了5-HT1A受体的数量和反应性,从而使抑制5-羟色胺信号传导的负反馈回路安静了下来。
除了5-羟色胺,包括谷氨酸、氨基丁酸和多巴胺在内的神经递质,也在自杀行为的背景下得到研究。特别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一些药物,例如能与谷氨酸受体NMDAR相互作用的氯胺酮和艾司氯胺酮,能够更好的降低临床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然而,关于这些神经递质的文献是相对不一致的,这促使着研究人员继续寻找新的机制来揭示自杀行为。
5-羟色胺
5-羟色胺信号的传导中断在自杀身亡者的大脑中反复被发现。
SERT
自杀身亡者的5-羟色胺转运体SERT的水平可能较低,它负责将5-羟色胺运送回突触前神经元。
5-羟色胺受体
在试图自杀或自杀身亡的人体内,5-羟色胺受体5-HT1A和5-HT2A的水平可能更高。
—
LISA CLARK
预测和干预自杀的工具
精神病学家大卫·布伦特(David Brent)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是大约在他40年前担任住院医生之际。布伦特被派往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儿童医院,来对接因试图自杀,服药过量而入院的年轻人。他必须决定谁会被转到精神科病房,谁可以安全回家。“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很好的方法来做决定,”布伦特说,他现在是匹兹堡大学的一名教授。当他了解到其他临床医生是如何做出类似决定时,“我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没有雇员真正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好公司’工作。”
对于试图为自杀风险人群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两难处境。今天的临床医生常常依赖患者主诉的状况来报告患者的意图,来决定应该给予的干预措施。但是这种方法有局限性。一项2019年关于自杀想法的荟萃分析发现,大约60%的自杀者在死亡前几周或几个月被医生询问时,都否认有自杀想法。
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寻找方法,将神经生物学的发现转化为生物标记的识别,从而预测自杀行为的发生。考虑到HPA轴与自杀密切相关,它长期以来一直是这项研究的重点,而且有一些证据表明,血液中过高或者过低的皮质醇水平也可当作一种生物标志物。例如,几个月前,布朗特和他的同事发表的一项针对青少年的长期研究结果称,一个人的基准皮质醇水平可拿来预测未来的自杀意念,如果皮质醇增加,在未来几年内的自杀意念也会更强烈。
皮质醇测试也可能帮助到预测自杀的其他手段,例如有关社会和学术压力的问卷。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问卷数据可以很好地预测有心理问题的220名女生中,哪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自杀意念,但却很难预测哪些人真的会实施自杀。当研究人员把视线锁定到那些在实验室测试中表现出皮质醇反应迟钝的女生时,问卷数据能更好地预测自杀行为。
除了压力反应之外,其他研究组也尝试识别与神经传递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几年前,曼恩的研究小组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成像技术,对100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中脑5-HT1A 5-羟色胺受体水平进行了评估。科学家们发现,较高的5-HT1A水平预示着未来两年更强烈的自杀意念和更致命的自杀行为。去年夏天,耶鲁大学神经心理学家伊莱娜·艾斯特里斯(Irina Esterlis)领导的研究组报告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技术检测到的谷氨酸受体mGluR5的水平,与创伤后应激障碍者目前的自杀意念有关——尽管这个结果对重度抑郁症患者并不适用。
对于这种生物化学特征在评估自杀风险方面的潜力,研究人员意见不一。药理学家格雷格·奥德韦(Greg Ordway)表示,虽然生物学可能会识别出有自杀倾向的人,但不太可能产生一个或几个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揭示一个人是否即将结束生命。“自杀是极难预测的。”他说,“人们总是在尝试这样做——像我这样的人一直在寻找自杀的标志物。但在现实中,我不觉得我们真的有可能找得到。”
评估即时风险最有希望的一些工具可能来自神经科学的其他领域,这些领域测量的是大脑中更复杂的情感信号,而不是生物化学信号。2017年,布朗特与神经学家马塞尔·贾思特(Marcel Just)等人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在34个被试思考“死亡”、“麻烦”和“无忧无虑”等词汇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成像。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处理数据,研究组试图区分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自我报告有自杀意图的人和没有自杀意图的人,准确率高达91%。在那些有自杀意图的人中,研究组以94%的准确率预测了那些已经尝试自杀的人。
研究人员最近从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获得了380万美元的支持,用于扩大该项目的规模,并计划对不同心境障碍的患者和非患者进行长期监测。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希望扩展他们的工具,以识别未来可能自杀的人,而不单单是扫描时正在考虑自杀或过去曾有过自杀行为的人。贾思特说,该团队还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一种比MRI更便宜、更方便临床使用的技术,如脑电图(EEG)。
梅尔亨姆说,在未来几年里,她希望这些技术的结合将改善预测方法。在2019年,她和同事们发表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改进了现有模型的准确性和性能,根据抑郁症患者跟着时间的变化,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特征的不同来预测自杀行为。她表示,将这种容易收集的临床数据,与来自脑部扫描或其他诊断测试的生物信息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类似预测性研究对预防自杀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它们在评估自杀风险方面的潜力。“当我们将生物标志物引入研究,就像任何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病耻感就会在患者的层面上降低,”梅尔亨姆说。听闻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自杀背后的生物学原理时,患者常常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他们性格中的缺陷,并为此感到内疚。而这也是我们想要对抗的病耻感的一部分。”
作者:Catherine Offord | 封面:Owen Gent
翻译:ZIWEN | 审校:亦兰 | 排版:小葵花
编辑:EON
原文:https:///features/what-neurobiology-can-tell-us-about-suicide-66922
本文基于BY-CC协议翻译